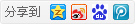6月12日,针对近期全国多地接连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明确对重大、敏感的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可按《刑事诉讼法》规定实行提级管辖。
经过多年法律文本框架的构架,特定刑事案件类型的法律规定日臻完善,从实体到程序总体来看基本有据可循。但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在某一时期由司法机关下发通知以重申和明确对某类案件的处理原则与方法,其初衷或在于表示司法机关对热点社会问题的关切,但顺着相关通知文本的思路,也可大致梳理出一条类似案件在司法实务中的走向,以及可能遭遇的干扰。
刑法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置于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下,罪名设置清晰。但正如对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的普遍公众忧虑所指,个案所反映出的问题可能会远超出事故本身,先前安全监管的缺位极有可能事涉“失职渎职、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包庇纵容”等行为,事发后更是可能出现遮掩真相(甚至是遇难人数)、阻碍救援、干扰调查等情况。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所可能涉及的罪名,需要考虑“贪污贿赂行为与事故发生有关联性,职务犯罪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等问题。安全生产一旦成为“事故”,则不可避免走向刑事司法调查,而导致生产不安全、干扰事故调查、影响案件侦办的诸多因素,亦是司法所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之所以选择提级管辖,或应视为司法机关在现有司法环境之下,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强调与保障。在刑诉法23条的规定中,上级法院在认为“必要时”,即可启动提级管辖;而下级法院在“认为案情重大、复杂”且需要时,可请求将案件移送上级法院。而最高法对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中,则将提级管辖细分出“重大、复杂案件”、“新类型的疑难案件”或“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几种情况。观此次最高法所发通知,具体的表述为“重大、敏感的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严格来说,“敏感”一词并非严格的法律用语,界定案件敏感与否,可能会存在适用上的争议。
2013年1月,最高法相关会议,曾有“依法妥善处理好重大敏感案件”的提法。5月,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讲话中亦有“做好敏感案件舆论引导工作”的表态。作为非法律用语存在的“敏感案件”,具体到司法实务中如何认定和处理,值得深究。此次最高法通知对需提级管辖的相关案件,用“影响大,社会关注,政策性强,专业性程度高,责任认定难度大”来描述,加之此类刑事案件多与职务犯罪等相伴而行,由此或可窥见辨别案件敏感与否的模糊标准。案件关注度的高低,以及案件受干扰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应该算是案件敏感的主要成因,亦是提级管辖的必要性所在。
必须要看到,重大敏感案件提级管辖,旨在求解的,不仅是专业程度与法律责任的认定难题,更在于试图攻克相关案件背后所遭受的权力干扰。不少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或突发事件的事后调查,遭遇到的阻力与困顿,为公众所熟知,调查久拖不决,问责避重就轻,真相在逃公信溃失……未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公共事件所面临的种种,在进入司法程序后不会自动止步,只会同样存在,且愈演愈烈。当然,重大敏感案件依“通知”而提级管辖的背后,还有其他类型的重大、敏感案件在遭遇着“立案难”,以及艰难立案之后的司法流程“幕后操控”。已有的案例,包括但不限于三鹿毒奶粉家长的维权诉讼、一些地方的拆迁案件,以及各种迎合地方政治、经济需求的区域性敏感。
屡屡发文强调和重申,正是因为既有的法律程序与实体现状不尽如人意。用敏感与否来对案件进行非法律的界定,以及用提级管辖的方式所要应对的,本身便是司法排除干扰的无力与困顿。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句现行《宪法》对司法权的授权性规定,落到人间之后的处境,可谓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甘苦自知,进而影响到每个人。